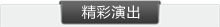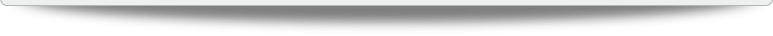【新快报】星海和它的朋友圈(三)
作为广州最出名的文化地标之一,星海音乐厅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迎来众多国际国内的大师级音乐家和演奏家。他们携传奇而来,又让星海成为传奇的延续地。本月,我们将一起回顾今年内造访星海的12位大师级音乐家以及他们留下的美妙音符。
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呼呼的北风肆虐地扑打着门窗,像莽撞的醉汉,找不到归家的房门。这时候,偎在被窝里,听我的幻想和梦想,听我的渴望和企盼,除了会被音乐有所震撼之外,也许还能勾引出你自己许多逝去的往事。一下子,旋律和窗外的寒风交织在一起,显出几分悲凉、苍凉和清凉来。这时,你的心里不是稍稍温暖,而是觉得更加寒冷,一种森森的感觉袭上心头,就像《幻想交响曲》第三乐章中定音鼓最后的那几声凄厉的号声,飘渺地消逝在空中。幻想,有时不是那么好玩的,有人说幻想成就了我,让我的音乐迸发出璀璨的火花,织出一片云锦来;对于常人,幻想却常常会害了自己,我们以为能从大海里真的捞出普希金的金鱼来,其实最后捞出的不过只是千疮百孔的破鱼网和发腥的海草。
贝多芬虽说也狂放,但更多的是高傲,是对现实世界的投入,而我则是将音乐挥洒在想象的世界里。
我一生都在追求爱情,只是所追求的爱情和一般常人所理解的恋爱、结婚以至到居家过日子的那种平常意义上的爱情,并不一样。我所追求的爱情是想象世界中的,就像一个画家永远是把他心目中的爱情涂抹在画布上。我最喜欢在下着滂沱大雨的时候到蒙玛特墓地去,因为那里埋葬着我死去的前妻,“人世间只有活在心中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我想重点谈谈下半场曲目《幻想交响曲》。这首交响曲之所以在音乐史上地位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种全新的器乐语言。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有能力传递柏辽兹心中那炽热的感情(这首交响曲据说是柏辽兹单相思的产物),使音乐与文学更为接近,力图将文学中所描写的生动而具体的形象,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使器乐的表现力更加具体和深刻。
进一步说,柏辽兹把精神意象神奇地转化为了声音,机智地运用乐器法的才能,以及明显现代性的音乐色调观念,他以一种完全是革命的方式开发管弦乐:他不单要求两架竖琴、一支英国管、一支降E调单簧管,两支奥非克莱德号、四面定音鼓和一大串的打击乐器,而且要求每一件乐器去完成以前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事情;他完全从实用的观点来运用单个的声部,他把音色、声区和力度精巧结合而创造管弦乐的声音,这是和其他古典大师不同的地方。
我的履历包括:现任伦敦皇家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曾任蒙特利尔交响乐团艺术总监25年之久;与费城乐团刚庆祝了合作30周年的里程碑,被誉为费城乐团桂冠指挥。每一个演出季,都与芝加哥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合作。曾为Decca、德国唱片公司、EMI、Philips与Erato唱片品牌共录制了两百多张唱片,屡获奖项与殊荣,包括两项格莱美大奖。
外界对我录制的德彪西、柏辽兹和比才等法国作曲家的作品,给予好评。法国派音乐家的那种浪漫气质,我可能把握得较为充分。
7月24日·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与李云迪携手美国青年交响乐团,演出曲目:谭盾《帕萨卡里亚——风与鸟的密语》、贝多芬《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柏辽兹《幻想交响曲》
e小调大提琴交响协奏曲(作品125)是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14年后创作完成的,相当于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同是也是我最后一首大提琴曲。
作品虽然很快便被写了出来,但遗憾的却是在1952年首演时没有能够获得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大提琴独奏部分被写得技巧过于艰深和复杂,另外音乐也缺少有机的完整性,因而观众自然也就是反应相当冷淡。此后,在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力帮助下对作品进行了重大修改,甚至许多段落还推翻重写。由于改写后的音乐不仅独奏声部的乐思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作为协奏的整个乐队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品中高度的戏剧性内容和形象的交响发展很有些近似于我创作的第五与第六交响曲,其中鲜明的音乐主题和抒情的叙述乐段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最后一部作品《第七交响曲》,由此,我在最后定稿时将原来的名称“第二大提琴协奏曲”改变成为《大提琴交响协奏曲》,并将它题献给了罗斯特罗波维奇。后来这首《交响协奏曲》也正是在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广泛演奏和大力宣传推介下才得以名声远扬,并成为了世界大提琴音乐文献中的经典之作。
此曲在美国出演时所得的评语是“这首充满活力与变化的乐曲,犹如一座主题与插句的金矿”,这句评语正好明晰地表达了这首乐曲的性格。
普罗科菲耶夫:这乐曲充满活力与变化,犹如一座主题与插句的金矿
大提琴能演的曲目很少。浪漫主义时期最多,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时期较少,只有巴赫和海顿,那时大提琴基本还是伴奏乐器,贝多芬之后才成长为独奏乐器。在没法选择的情况下,我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浪漫时期作品。但巴赫的六首“大无”就像我们的圣经,无可替代。
从整体的音乐角度来说,我喜欢巴赫、勃拉姆斯、肖邦、马勒、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慢乐章,太美太好听了。如果去荒岛只能带一首曲子,我一定带它。
现代派从勋伯格开始走弯路,没走多久又开始回转了,潘德列茨基也说,“我对自己前半生的作品开始有点怀疑。” 他也在往回走。
学院派过于强调技术,是死路一条,完全是在意淫。有时我跟年轻作曲家说,有些段落你写得很好听,为什么非要去写那些难听的?他回说,不敢写好听的音乐,写好听了事业就会被“抹杀”。现在的国际潮流是,复古派不流行,你必须写得人听不懂,一定要达到某种格式才被认为是创新。这是文化堕落的一种,好吃的吃腻了,开始吃难吃的。但他们忘了作品一定要靠我们来演,作品要真正成功,必须要演奏家喜欢,才能真正流传。
好在作曲家们终于反应过来音乐不是算术,不是数学,你写得再复杂,理论上有再多创新,不好听都没用。现代音乐常常放弃感性,完全是理性探索,这在数学和科学上没问题,但音乐一定要用感性做最后的衡量标准。
9月11日·大提琴家王健与广交合作,演出曲目:普罗科菲耶夫《交响协奏曲》、肖斯塔科维奇《C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普罗科菲耶夫《交响协奏曲(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5号)
王健:音乐一定要用感性做最后标准
埃克托·柏辽兹
(法国作曲家,1803-1869)
(法国作曲家,1803-1869)
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呼呼的北风肆虐地扑打着门窗,像莽撞的醉汉,找不到归家的房门。这时候,偎在被窝里,听我的幻想和梦想,听我的渴望和企盼,除了会被音乐有所震撼之外,也许还能勾引出你自己许多逝去的往事。一下子,旋律和窗外的寒风交织在一起,显出几分悲凉、苍凉和清凉来。这时,你的心里不是稍稍温暖,而是觉得更加寒冷,一种森森的感觉袭上心头,就像《幻想交响曲》第三乐章中定音鼓最后的那几声凄厉的号声,飘渺地消逝在空中。幻想,有时不是那么好玩的,有人说幻想成就了我,让我的音乐迸发出璀璨的火花,织出一片云锦来;对于常人,幻想却常常会害了自己,我们以为能从大海里真的捞出普希金的金鱼来,其实最后捞出的不过只是千疮百孔的破鱼网和发腥的海草。
贝多芬虽说也狂放,但更多的是高傲,是对现实世界的投入,而我则是将音乐挥洒在想象的世界里。
我一生都在追求爱情,只是所追求的爱情和一般常人所理解的恋爱、结婚以至到居家过日子的那种平常意义上的爱情,并不一样。我所追求的爱情是想象世界中的,就像一个画家永远是把他心目中的爱情涂抹在画布上。我最喜欢在下着滂沱大雨的时候到蒙玛特墓地去,因为那里埋葬着我死去的前妻,“人世间只有活在心中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迪图瓦:他的音乐和他自己,都生存在他的想象世界里
夏尔·迪图瓦
(瑞士指挥家,1936-)
夏尔·迪图瓦
(瑞士指挥家,1936-)
我想重点谈谈下半场曲目《幻想交响曲》。这首交响曲之所以在音乐史上地位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种全新的器乐语言。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有能力传递柏辽兹心中那炽热的感情(这首交响曲据说是柏辽兹单相思的产物),使音乐与文学更为接近,力图将文学中所描写的生动而具体的形象,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使器乐的表现力更加具体和深刻。
进一步说,柏辽兹把精神意象神奇地转化为了声音,机智地运用乐器法的才能,以及明显现代性的音乐色调观念,他以一种完全是革命的方式开发管弦乐:他不单要求两架竖琴、一支英国管、一支降E调单簧管,两支奥非克莱德号、四面定音鼓和一大串的打击乐器,而且要求每一件乐器去完成以前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事情;他完全从实用的观点来运用单个的声部,他把音色、声区和力度精巧结合而创造管弦乐的声音,这是和其他古典大师不同的地方。
我的履历包括:现任伦敦皇家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曾任蒙特利尔交响乐团艺术总监25年之久;与费城乐团刚庆祝了合作30周年的里程碑,被誉为费城乐团桂冠指挥。每一个演出季,都与芝加哥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合作。曾为Decca、德国唱片公司、EMI、Philips与Erato唱片品牌共录制了两百多张唱片,屡获奖项与殊荣,包括两项格莱美大奖。
外界对我录制的德彪西、柏辽兹和比才等法国作曲家的作品,给予好评。法国派音乐家的那种浪漫气质,我可能把握得较为充分。
7月24日·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与李云迪携手美国青年交响乐团,演出曲目:谭盾《帕萨卡里亚——风与鸟的密语》、贝多芬《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柏辽兹《幻想交响曲》
柏辽兹: 一流的“调色师”,他让音乐与文学更接近
普罗科菲耶夫
(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1891-1953)
普罗科菲耶夫
(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1891-1953)
e小调大提琴交响协奏曲(作品125)是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14年后创作完成的,相当于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同是也是我最后一首大提琴曲。
作品虽然很快便被写了出来,但遗憾的却是在1952年首演时没有能够获得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大提琴独奏部分被写得技巧过于艰深和复杂,另外音乐也缺少有机的完整性,因而观众自然也就是反应相当冷淡。此后,在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力帮助下对作品进行了重大修改,甚至许多段落还推翻重写。由于改写后的音乐不仅独奏声部的乐思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作为协奏的整个乐队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品中高度的戏剧性内容和形象的交响发展很有些近似于我创作的第五与第六交响曲,其中鲜明的音乐主题和抒情的叙述乐段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最后一部作品《第七交响曲》,由此,我在最后定稿时将原来的名称“第二大提琴协奏曲”改变成为《大提琴交响协奏曲》,并将它题献给了罗斯特罗波维奇。后来这首《交响协奏曲》也正是在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广泛演奏和大力宣传推介下才得以名声远扬,并成为了世界大提琴音乐文献中的经典之作。
此曲在美国出演时所得的评语是“这首充满活力与变化的乐曲,犹如一座主题与插句的金矿”,这句评语正好明晰地表达了这首乐曲的性格。
普罗科菲耶夫:这乐曲充满活力与变化,犹如一座主题与插句的金矿
王健
(大提琴家,1969-)
(大提琴家,1969-)
大提琴能演的曲目很少。浪漫主义时期最多,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时期较少,只有巴赫和海顿,那时大提琴基本还是伴奏乐器,贝多芬之后才成长为独奏乐器。在没法选择的情况下,我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浪漫时期作品。但巴赫的六首“大无”就像我们的圣经,无可替代。
从整体的音乐角度来说,我喜欢巴赫、勃拉姆斯、肖邦、马勒、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慢乐章,太美太好听了。如果去荒岛只能带一首曲子,我一定带它。
现代派从勋伯格开始走弯路,没走多久又开始回转了,潘德列茨基也说,“我对自己前半生的作品开始有点怀疑。” 他也在往回走。
学院派过于强调技术,是死路一条,完全是在意淫。有时我跟年轻作曲家说,有些段落你写得很好听,为什么非要去写那些难听的?他回说,不敢写好听的音乐,写好听了事业就会被“抹杀”。现在的国际潮流是,复古派不流行,你必须写得人听不懂,一定要达到某种格式才被认为是创新。这是文化堕落的一种,好吃的吃腻了,开始吃难吃的。但他们忘了作品一定要靠我们来演,作品要真正成功,必须要演奏家喜欢,才能真正流传。
好在作曲家们终于反应过来音乐不是算术,不是数学,你写得再复杂,理论上有再多创新,不好听都没用。现代音乐常常放弃感性,完全是理性探索,这在数学和科学上没问题,但音乐一定要用感性做最后的衡量标准。
9月11日·大提琴家王健与广交合作,演出曲目:普罗科菲耶夫《交响协奏曲》、肖斯塔科维奇《C大调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普罗科菲耶夫《交响协奏曲(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5号)
王健:音乐一定要用感性做最后标准

相关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