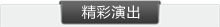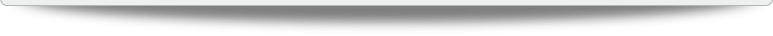俄罗斯学派最后一人

普雷特涅夫是谁?就算外界载誉等身,他对自己的批注总是这样:“我只是一个音乐家。”或者以玩笑的口吻说:“就是一个丑陋又讨厌的老头子,一点儿都不懂得体谅音乐厅的座位何其不舒服,既不让听众好好睡一觉,还一直在前面制造噪音!”
接受过全球数不尽的媒体访问,可是普雷特涅夫完全否认,也不相信那些文章所描述的,竟然会是自己。我同意。我同意媒体上看到的普雷特涅夫形象,的确不是我认识的那一个普雷特涅夫。但是他更不像自己所言,只是一名单纯的音乐家,或是个只会制造噪音的老家伙。
俄罗斯钢琴家、教育家弗拉先科(Lev Nicolayevich Vlasenko, 1928-1996)曾经说,当一个音乐家的演奏碰触到他的心灵深处时,“我会起鸡皮疙瘩,说不出话来,只求这个奇迹不要结束,希望它持续下去,至少再持续一下子……这是演奏音乐最珍贵的时刻”。看到这句话时,我也起了鸡皮疙瘩:这不正是我第一次在音乐厅接触普雷特涅夫音乐的感觉与心情吗?于是除了踏入普雷特涅夫的音乐世界,我也开始探索俄罗斯文化,尝试了解它所强调的精神面所言为何。普雷特涅夫以他的艺术带我走进俄罗斯文化,认识俄罗斯文化本质的一面。
对于普雷特涅夫的音乐,一般乐评人除了承认他的技巧的确无可挑剔之外,常常把“自我”、“怪异”、“酷”、“标新立异”、“冷”……等形容词加在他身上。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发现普雷特涅夫的艺术其实完全根植于俄罗斯传统文化思想。他的艺术养分来自传统,但是天赋让他开出前所未见的艺术花朵;因为前所未见,反而被认为“非传统”,这完全是从表面认识造成的误解。
在活跃于当前国际乐界,比普雷特涅夫年轻一代的俄罗斯音乐家身上,如:马祖耶夫(Denis Leonidovich Matsuev)、卢冈斯基(Nikolai Lugansky)身上,我感觉不到这些来自俄罗斯传统艺术观念的声音,更别说是对艺术态度过于轻率的贝瑞佐夫斯基(Boris Vadimovich Berezovsky)。或许正如普雷特涅夫所说,所谓的“俄罗斯学派”至今已经不复存在,而普雷特涅夫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在在证明他是俄罗斯学派的最后一人,这也是我觉得普雷特涅夫值得一写的原因。
一回在开往圣彼得堡的夜车上,我和俄罗斯国家管弦乐团(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即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也有人译作“俄罗斯国家管弦乐团”)首席,也是普雷特涅夫从中学时期就认识的好友布鲁尼(Alexey Mikhaylovich Bruni)聊起普雷特涅夫几天前在莫斯科的一场演出。“在我的观念里,”我说:“根本不能以一张唱片、一场音乐会来评断普雷特涅夫的艺术。因为他在每一次演出里,总是尝试创造出新的东西。”布鲁尼微笑点头,表示完全同意我对普雷特涅夫艺术的观察方向。基于这点认知,这本书的结构与写作方法不会着眼在评析普雷特涅夫某一张唱片或某一场音乐会,而是融会长时期的观察,从大方向分析。同时,也希望我能刻画出一名杰出音乐家活生生的一面,引领爱乐者更深入了解我所认识的普雷特涅夫,而不是看到一名被神化与过度包装,供奉在神坛上膜拜的偶像。
(本文为陈效真所著《音乐是我此生的使命─普雷特涅夫组曲》一书的导奏,文章原标题为《为什么要写普雷特涅夫?》)

相关音乐会
|